2020年底,《(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2024年1月,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重要阶段性成果,《(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上下册完成出版。《(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既是编纂中的《(新编)中国通史》的前期成果,也是一部独立成书的简明中国通史著作。本文试从几个学术角度对“纲要”进行简要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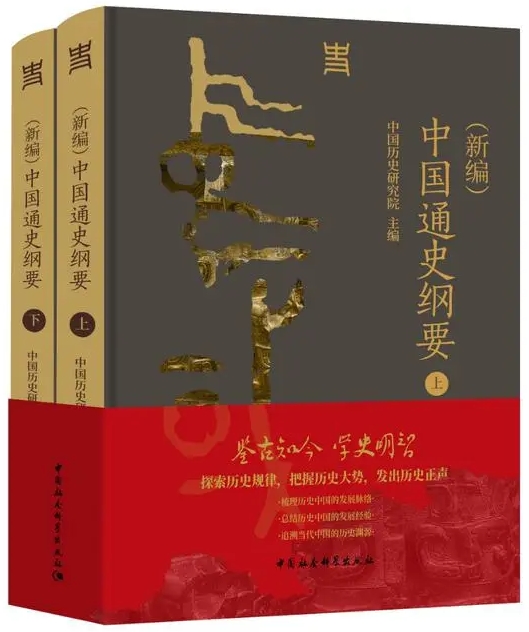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 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供
编纂中国通史的时代意义
被司马迁赋予“通古今之变”史学旨趣的通史撰述,是中国史学延续数千年的优良撰史传统。《资治通鉴》“三通”《史通》《文史通义》、郑樵申论的“会通之义大矣哉”、王夫之阐述的“通古今而言之”等,都从撰史实践和史学观念上不断丰富、强化着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内涵。自20世纪初梁启超倡议中国“新史学”以来,近代中国史学学习、借鉴西方史学的“趋新”之势,导致传统史学在许多方面发生很大变化,如在史观上从经学主导的旧史观变为以进化史观或唯物史观为核心,在史书体例上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变为以章节体为主,在文体上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然而,通史意识及编撰中国通史的努力却并未因新旧史学转换而缺失,集贯通古今、宏大叙事、理论阐释、现实诉求等要素于一身的通史撰述,在近现代中国史学语境中反而备受关注。
事实上,梁启超当年倡导“新史学”的起因,就是因为要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对夏曾佑、吕思勉、邓之诚、张荫麟、钱穆等史家的中国通史撰述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五六十年代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等,90年代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不仅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更加重视具体研究、专题研究、微观研究,史学研究“碎片化”现象随之日渐突出,此前用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得出的若干重要历史理论认识不断受到质疑,二十多年来由主流史学界撰写的有影响的中国通史撰述基本没有出现,倒是域外学者撰写的一些多卷本中国史通史类著作相继被引进、翻译出版,其中所反映出的中国观,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线等重大问题的各种解读,引发了不少混乱认识,国内史学研究“碎片化”现象不仅难以应对外来中国史理论建构的冲击,而且在掌握历史话语权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缺失。这些现象与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时期的当代中国的时代要求并不相符。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需要贯通古今的历史撰述作为其学术依托和呈现载体;对历史的现实诉求与时代关怀,需要对整体历史发展过程概括和总结出一般性认识;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离不开通史格局和通识意识;基于国家民族立场解答与回应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亦需扎实的实证研究、充分的理论支撑和长时段的开阔视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亟待推出集大成的中国通史之作。
“纲要”在中国史学界二十多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材料等各方面开拓创新收获的基础上,详略得当地叙述从远古文明起源到当下新时代的中国历史发展,力图展现国家层面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古代、近代和现当代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阐明“大一统”观念、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关系、王朝更迭、制度演变、国家政权性质、近代民族复兴等宏观或中观问题。“纲要”在历史解释、理论阐发、历史分期等方面表现出了具有时代高度的主体意识和叙事特点,努力践行了既有“通史”之名又有“通史”之实的学术追求,契合了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要求。

商鞅方升 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供

西汉“滇王之印” 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供
创新性运用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在中国古史分期、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更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同时,“五种生产方式”说中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问题也相继受到质疑。“纲要”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应该是读者非常关注的。书中“总序”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该书的“核心指导思想”,但该书各章并未像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通史撰述那样,以某种社会形态冠名章题,而是以不同朝代或政权先后,分时代依次分章命题,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特点则结合正文中的史实进行论述,并且,在每章的“章首语”中都会阐明该章所述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如第一章“史前时代”,该章“章首语”谓之“原始氏族社会”;第二章“夏商时期”,谓之“奴隶制社会”,也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初期阶段”;第三章“西周、春秋和战国”,“章首语”谓之“宗法封建制”;从第四章“秦汉统一”开始,直到鸦片战争前,分别是“地主封建制”的早期发展、成熟与变革、鼎盛和衰落阶段;1840-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外,书后“附录”“大事编年”则以“文明起源与奴隶制国家形成”“宗法封建时代”“地主封建制的早期发展”“地主封建制的成熟与变革”“早期近代化与封建制鼎盛而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等标题为纲,编年分述中国历史大事,进一步明确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中的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
如此谋篇布局,可以看到著者的深刻用意:第一,历史解释的对象、基础、依据是历史事实,《(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以历代王朝政权形式为全书“总目录”,以各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大事构成全书章节框架,在叙述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解释,而不是用史实服务于理论去“强制阐释”。这样做的效果是,不至于因论证理论而忽视史实(如曾经因过分突出“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而弱化“王朝体系”),也不至于因照顾理论框架而分裂史实框架(如以往因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理论而在历史叙事中将清朝“一分为二”),从而在中国通史的历史叙事中更有针对性地、更灵活地、实事求是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撰史宗旨,力图避免曾经存在的教条化、公式化的不足。
第二,该书在运用社会形态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阐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更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更重视吸收近些年来中国史家以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而构建的更具“中国化”的古史分期新说。中国古代社会有无奴隶制的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纲要”基于“奴隶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剥削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认识,将夏商时期确定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但是强调“与古希腊、罗马等的古典奴隶制不同,夏商奴隶制主要体现为世袭君主制下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奴隶制”。如何理解奴隶制,怎样确定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该书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值得重视。封建社会始于何时,是中国古史分期的焦点问题。“纲要”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西周即采用了“西周封建制”,值得关注的是,“纲要”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分为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法封建制”和秦汉统一之后的“地主封建制”。“西周封建制”是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坚持的一种古史分期观,而“宗法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则综合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古史分期理论的新观点而成,这些观点更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把这些观点运用于中国通史撰述中,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创新之举。此外,曾经在社会形态理论语境中有过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其所收获的扎实的研究成果,在“纲要”中均有体现。如“纲要”对秦汉时期“确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日益发展,等级土地所有制不断推广”、隋至唐前期“土地国有制较为发达”等问题的论述;再如对两宋“市镇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以至“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等现象的阐发,都反映出数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供
在通史中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以今天的认识高度阐述、论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通史撰述的核心内容之一。“纲要”重在阐明中国民族史的主流认识,吸收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梳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力求在中国通史的宏大叙事中立体展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以古代史为例,如秦汉时期“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国家,从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各个民族逐步交融,疆域不断开拓,形成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和人口流动促进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汉化仍成为民族交融的主流”;隋唐五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辽、夏、金时期“既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也是南北政权相互对峙的时期”;清朝统治者“继承中原王朝治国理念,选择以正统儒学为政权指导思想”,“有效维护并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纲要”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阐述,传递了中国民族史观之正声,具有在民族史问题上正本清源的作用,也是对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出现的关于中国民族史问题的各种错误观点、混乱认识的回应。
考古学研究与中国通史撰述有机结合
史前时期因传世文献记载中多有神话传说而不尽可信,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适时填补了这个空缺。率先尝试由考古学家用考古学研究成果书写中国通史中的史前时代,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1994年初版),该卷由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主编并撰写。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研究极受重视,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许多地区都开展了大规模遗址发掘,不仅在发掘规模和研究水平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基本廓清了主要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发展谱系,并对此做出了初步的理论归纳。由考古学家在中国通史中撰写中国史前史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远古时代”卷的问世,不仅在以往中国通史撰述中开创了先例,而且在考古学研究中也是一项创举。自那以后,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更为突出的研究成就,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实施,经过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为研究手段、以探索中华文明源头及早期国家形成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不懈努力,中国史前史展现出了更清晰的多元轮廓,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有了更充分的考古学依据。“纲要”中的“史前时代”同样是以考古学研究成果构成了史前史叙事主体内容,又一次践行了在中国通史撰述中阐述中国远古历史的考古学话语。
尽管白寿彝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远古历史”部分是以一卷成书,“纲要”中的“史前时代”在其书中是以单篇成章,两书体例不同,在篇幅上也不成比例,但仍可对二者稍作对比。前者主要叙述了黄河、长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每个时代按不同阶段详述,再按方位逐一述及周边地区;后者从中国人的起源到农耕社会的形成、从早期国家的形成到王朝的诞生为阐述主题,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更加明显。前者重点介绍了以“半坡类型”为主的仰韶时代前期、仰韶晚期、龙山时代以及“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特点是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清理史前史的发展脉络;后者则基于几十年来的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从考古学文化中概括出早期农耕文明中的多元文化传统、“满天星斗”的区域性“古国”政体或“早期国家”的“最初的中国”形态,使追寻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雏形的学术目标更加明确。此外,从“纲要”“史前部分”的历史表述中可以发现,考古学话语与历史学话语的兼容性明显加强,考古学成果构建的中国史前文明图景更成熟地融入中国通史撰述中。通过比较二书内容,明确可见其成书间隔20年间考古学构建中国远古文明历史体系的诸多收获,而考古学研究成果融入中国通史撰述中的适应度也得以明显提升。
“纲要”所表现出的创新特点远不止这些,如力图以中国通史撰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现实取向,考察近代以来经过艰苦奋斗终使中华民族步入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曲折过程,论证近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主导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在阐述中国历史各阶段发展时同步关照世界史的比较、互鉴意识等,都与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直接关系,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主流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
本文刊发于《光明日报》2024年7月11日第11版;作者张越,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4-07/11/nw.D110000gmrb_20240711_1-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