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写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学者型的高级干部。他在退休之前,担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但他最初的知识底蕴则为中国传统文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级干部逐渐年轻化、知识化,许多各行各业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适应时代的需要,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完成了从专业技术工作到管理工作的转型。稍微有点儿传奇的是,做了十年广东高院院长的吕伯涛,是启功先生的弟子。

吕伯涛(左)与启功(右)
一、与我之交往
吕伯涛比我长七岁,他和我的关系是师兼友。大约百分之三十为师的成分,百分之七十是友的成分。他与我之间,既没有鲁迅云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真挚性;我与他之间,也没有舒芜云冯雪峰“平生交谊师兼友,一夕谈谐始亦终”的深刻性。但我在几十年的时光中,作为政治舞台下的看客,眼瞧着他一路走下去,很是佩服。
1981年夏天,吕伯涛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公安系统工作。本来他可以留校教书或去中华书局,但这两个单位都不能马上解决家属和子女户口问题,他便来到公安部,先去国际政治学院报到,后在部办公厅落脚——后者解决户口问题稍快一点儿。
个子不高、身材偏瘦的吕伯涛,一有闲空儿就钻进我的办公地点——群众出版社资料室。这个资料室的藏书比公安部图书馆的藏书多,在当时中央部委所属出版社的藏书中名列前茅。资料室的书放置在原清朝淳亲王府的大宫殿里,老吕一钻进去就没影了。他读书的目的性很强,主要翻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批评作品和一些体兼说部的著作以及各种文史类工具书。记得,他教会我查检陈垣所著《二十四史朔闰表》,把古代的干支日历转换成公元纪年纪月纪日——他是搞过史书的古代语言的白话翻译的,正好用得上。
吕伯涛在办公厅做调研工作,属于有条不紊、具有稳健风格的案牍干部,后来成长为公安部一支笔。他刻苦钻研公文写作业务,当办公厅主任时,有时白天钉班,夜里还要爬起来给领导起草文件。公文写作是一门学问,他在部里和广东高院给同事们上过公文写作课。我是从与他合作撰写《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一书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功力的。
《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作为一本研究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和程序的书,由商务印书馆向吕伯涛组稿。他公务繁忙,出差、开会、写文件、批阅文件等等,抽不出空来,于是赶鸭子上架,让我帮忙。他确定了这本书的逻辑框架,并写出了其中一节的样文,我们俩分头起草,最后由他统稿。这本书在布局上较有特色,安排了一般的法律史图书所不写的“状纸和讼师”“书吏、刑名师爷、衙役和长随”两节,并将其置于诉讼制度和程序上来描述。还安排了“行贿和勒索”一节,把官场腐败聚焦在点上,这样就使散在各节之中的关于官场腐败问题的描述有了结穴。按照商务印书馆的要求,书稿要写成侧重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通俗性学术著作。吕伯涛对我说:“不能只引用正史的材料,要更多地留意野史、笔记、小说之类;文体是说明性的,即使有议论也是说明性的议论。如果写成学院派的高头讲章,书就搞砸了。”吕伯涛早就在群众出版社资料室搞过调查,用该室的藏书,基本就可以解决史料问题。记得,我撰写了“审讯”一节,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王齐认为太长,建议厘为“审讯”“刑讯”两节。吕伯涛说,“审讯”一节更名“过堂”。我还能回忆起他选择更名时很高兴的样子。“过堂”是清代形成的对“审讯”的称谓,语言使用的生动、通俗程度要高于“审讯”。对我写的这一节,他做了许多修改、补充。譬如,溯源到《周礼》《后汉书》《晋书》《敦煌变文集》等等,发掘出与“过堂”相近的关键词“讯堂”“过案”。再譬如,吕伯涛读过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幕学家王又槐的《办案要略》,他对“叙供”的要求做了八条概括,这八条概括反映出他对公安工作中的记录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公安写作学认识。此外,从吕伯涛着墨之处,还能看出他对状纸、判词之类的诉讼文体的清晰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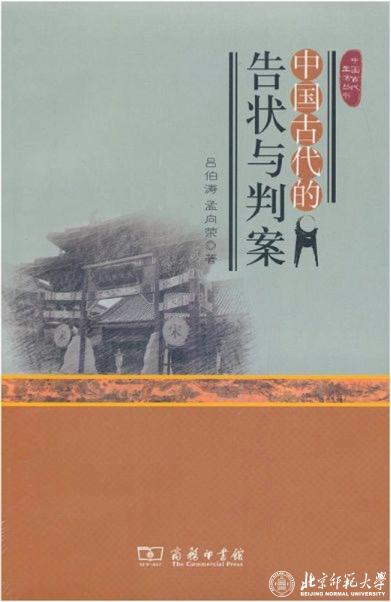
吕伯涛很会写作,对文章的结构安排、内容取舍、逻辑顺序、语词表达等等,都颇为考究。他的同窗好友赵仁珪曾夸奖道:“毕竟当过记者,文字就是溜,看着舒服。”相比之下,我的文字时有生硬之处,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与他在一个大院里居住时,我就常去他家做客;调动之前他来我家道别,告诉我他的去处;后来他来北京开会还经常用电话约我见面。老吕对学问之事每每耿耿于怀,有一次他从广东回北京时,对我说:“《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没有写司法官员的选任和擢升,是个缺憾。”我们交往之间偶有对文字问题的一些小争论,他总是慢条斯理、不多言,喜欢用一个词:“别抬杠。”
幽燕和南粤,天各一方。我们很少通音信,但我知道他的一些比较显赫的行迹:20世纪末,成功组织了对香港张子强犯罪案的审判,被最高法院授予个人一等功;21世纪初,成为首批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者。我为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感到骄傲和自豪。
二、与业师的交往
20世纪60年代,吕伯涛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过五年本科,三十五年后,他担任广东高院院长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到广州视察,与之相聚。老吕对我说:“当年许老师是我的古代汉语课任课老师。”似乎许嘉璐这次广州之行,从立法监督的角度,指导过吕伯涛的审判工作。
《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出版之时,老吕已经调往广东省工作。他没有时间回北师大,让我通过赵仁珪给启功、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韩兆琦五人题签赠书四本。记得聂、邓夫妇合赠一本。这是因为这五位先生在老吕读研时,同为他的业师。与吕伯涛走得最近的是韩兆琦。他的硕士论文是韩兆琦指导的。吕伯涛称呼韩兆琦“老师”,称呼其他四人“先生”。这似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资辈在韩、许以下称老师,资辈在韩、许以上呼先生。
韩老师是北京市高等教育领域的名师,天津人,高个子,口才好,擅长著述。凡对《史记》感兴趣的青年学子大抵都读过他写的书。也许因为我是他的邻居北京人,很喜欢他的天津口音以及豪爽大汉的样子。我曾经当面问过韩老师,蒋天枢先生希望你通读二十四史,你读了吗?他说,哪那么容易通下来,后来的情况你也知道。是的,现在的客观条件比韩老师成长的时期要好得多,但还是不能跟蒋先生那个时代的人比。吕伯涛在韩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他们都通读了前四史。20世纪80年代,他和韩兆琦合著出版了《汉代散文史稿》《左传国策故事选编》,这是老吕完全利用在公安部工作期间的业余时光完成的著述。在《汉代散文史稿》中,俩人提出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散文观:散文这个概念,本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够明确、文史哲尚未完全分家的汉代,散文的范畴应该划得稍宽一些。所以,章表奏疏、碑铭史传、书信杂记直至某些哲学著作,只要有一定的文学性或在散文发展史上发生过某种影响,都可以列入讨论的范围。当然也不是宽得没有限度,那些抽象的哲学论文,枯燥的经学著作,自然是不在列的。同时,散文又是和韵文相对的,所以那些讲究韵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辞赋,也可以不予讨论。《汉代散文史稿》本着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精神,写得线索明确、重点突出,尤其是从教学的角度,对所引原文做了许多注释放在各节之后,以便于初学者阅读。这种照顾治学通俗性的思路,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
师承关系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吕伯涛在公安部工作期间,去上海出差,造访过复旦大学的蒋天枢教授,带去韩老师的问候。从陈寅恪、蒋天枢、韩兆琦、吕伯涛一脉相承。据我所知,老吕也读师祖和师曾祖的著作。吕伯涛是韩兆琦取得硕士导师资格后的第一个研究生,被韩门后来的学生尊为“大师兄”。几十年来,他和韩兆琦一直保持师生的密切交往。记得,老吕的北京之家乔迁奥运村林萃路时,他对我说:“韩老师的新居离我这里不远,一回北京我就去看他。”对韩门的师弟、师妹们,他也曾为这些人毕业后的工作安排参谋出力。
吕伯涛对启功的感情十分深厚。这要从头说起。
我曾在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陆石家见过启功一次。记得,我对陆老爷子谈我刚刚读过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所论述的清代神韵说,沙发上坐着一位圆圆脸、笑容可掬、细心倾听却一言不发的老先生。事后,陆石说,那是启功。大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频繁地接触了吕伯涛的钢笔字,写得特别好。老吕书法家身份的显现,则在他从广东高院退休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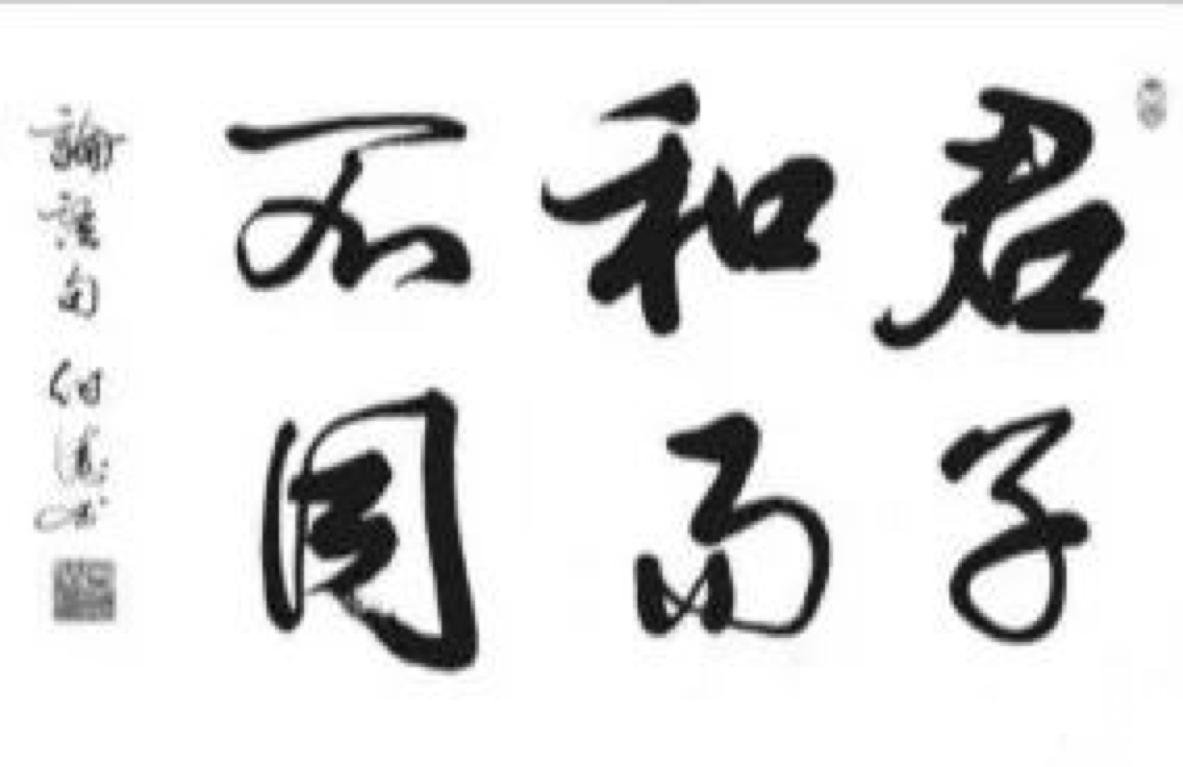
吕伯涛书法
早就听人讲过,启功并不要求他的弟子书法好,但对书法好的学生十分属意。何谓与启先生感情深厚?与他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书法艺术追求即为联系感情的纽带。2008年,吕伯涛出版了《雪泥鸿爪集——伯涛书影》(有幸得赐一本)。不懂书法的我,感觉他并未追随启功体。启功的字瘦秀,吕伯涛的字硕丽。吴南生赞其书法“恣肆”。这本书法集由漫书、联语、韵语、碑刻、题画、佳句、名篇七部分组成,里面包含自己的创作以及抄录古贤的名言隽句等。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吕伯涛读书时的研究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但他对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各种体裁的作品也是烂熟于心的。遗憾的是,这本书出版之前三年,启功就作古了。
吕伯涛对启功先生感情之深厚还体现在对师辈后事的安排上。陈垣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宗教史、元史、年代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创造性成就,著作等身。从解放前的辅仁大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师范大学,他任校长达四十五年,1971年以91岁高龄辞世。启功对恩师一直以最崇敬的心情,要求为陈垣塑像树立在北师大校园中,以供后学瞻仰。这件事,后来由吕伯涛代为奔跑完成。陈垣的一座全身铜像,树立在北师大校园中,一座半身铜像,安置在广东新会市陈垣故居前。启功在北京仙逝后,吕伯涛和北师大广东校友会一众同学,为恩师塑了两座半身铜像,一座安置在北师大校园中,一座安置在珠海市北师大分校校园中。老吕还为启功写了像赞,镌刻在塑像底部。《雪泥鸿爪集——伯涛书影》收录了这篇像赞:
维我百年名校大师辈出 吾师元白先生 巍峨其一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为先生亲拟之校训 亦先生一生之写照 吾侪有幸 或亲聆教诲 或忝列门墙 师德润泽心田 师恩没齿不忘 今特敬立先生铜像 以志纪念
赞曰铜像既铸 音容永驻 高山仰止 瞻趋如宿 铜像既成 丰碑永恒 景行行止 千秋范型
丙戌夏日弟子伯涛恭书
1980年,许嘉璐老师曾亲自题字“向荣吾弟指正”,赠我一本他的著作《古代文体常识》。按书中的分类,吕伯涛所写为哀赞。即《文心雕龙·赞颂》所云:“……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
三、与吴南生的交往
吴南生曾任广东省省委书记。他与习仲勋、任仲夷等人一起开拓了广东省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位资深老革命。吕伯涛与之交往的媒介是启功。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吴南生和启功就成为知己。吕伯涛于1995年由公安部奉调广东省担任省长助理时,启功修书一通,向吴南生介绍北师大“校友”吕伯涛“夙好文艺,慕望求教”。这是启功仅有的一次向老朋友吴南生推荐一位他肯定喜欢的新朋友。当时,吴南生刚刚从省政协的领导岗位退下来,正高兴自己能有时间读书写字之际,突然从年长自己十岁的故交那里得一年轻自己二十三岁的新秀,精神生活平添快乐而一扫寂寞。
在交往中,吴南生了解了吕伯涛。他说:“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又能重视和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这里,我说的“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而努力的人,他在任何领域里都能作出贡献的。”是的,老吕先从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跨入公安领域,又从公安领域跨入司法审判领域。2013年《中国古代的告状与判案》在大陆再版时(199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出过中文繁体字本),他为此书补入121张图片,使得原书有了图文并茂的特点。除了使用已有的书影和图片外,他还邀请一些艺术家根据书稿内容创作了不少随文走的生动有趣的画作。尽管此书所述皆为往古云烟,但吕伯涛退休后对公安、司法领域工作念兹在兹的珍惜留连之情还是从中折射出来。我从这本著作的前勒口个人简历处,看到他在广东高院工作期间主编的图书:《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改革研究》《适用合同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适用物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吴南生为《雪泥鸿爪集——伯涛书影》所写序言则著录了吕伯涛主编的《公正树丰碑——审理广东国投破产案始末》《商事审判研究》两种。这些恐怕不是他在广东高院期间的全部著述。记得,他刚刚卸任时,我在北京与之相见,说:“你是否写一部回忆录,题目叫《广东高院十年》。”他说:“不用了,我上任之初就开始组织法院的同志进行年鉴的写作,看后一目了然。”我还读过他公开发表的阐述新中国首任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的政法工作成就的长篇论文。吕伯涛卸任后,长时间担任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又写过什么大作?至于他在公安部工作期间的一些零星著述,我比较清楚。群众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出版过一本《史记酷吏列传选注》,书中注释错误较多,老吕为此写出专文在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发表,从《史记》语义疏解的角度,匡正此书的失误。他给《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古今中外名书禁书大观》《中国诗学大词典》等书写过赏析文字或辞条。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过说古论今的知识性杂文……可以说,吕伯涛通过这些既不出名、又无利益的细碎小活儿,尽可能地表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
吴南生还说:“在与伯涛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古而不论今’,可以从韩非子说到文征明,但不谈时政,不谈工作上的事,所以偶有见面,都相聚甚欢。”对老前辈的话我感触颇深。记得,我曾问过吕伯涛,广东省某些官员腐败的情况,他只吐出了三个字——“不自觉”,便缄默不语了。吴南生又说:“承伯涛厚爱,嘱为他的书法集写一小序,他在这本集中自撰的对联‘室依东壁图书府,心醉南国山水间’和联中四行长长的边跋,就是最好的序言。”录如下:
丁亥腊月 予卸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之职 得享闲云野鹤之乐 诸同事为我于法官学院图书馆东侧辟一室 权作饮茶会友读书涂鸦之所 予深为感动 回思知命入粤 转瞬十三载 人生如白驹过隙
诚然 唯岭南山水 年年苍翠 四季花果 岁岁喜人 可令游子忘归 遂作此联
伯涛谨识
“伯涛由儒变法”(吴南生语),末了,“永忆江湖归白发”,步入道家之境界,岂不复思儒法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