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2日晚,北京暴雨如注,雨点击打大地,如同激烈的枪声。诗人任洪渊在这个夜晚,21点49分,于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溘然长逝,享年83岁。他的女儿任汀告诉我,他走得安详平静。一颗奔腾跳跃的诗心,直到此刻,才肯平复、静止下来,像时间中的一块石头。

任洪渊生前近照
第二天早上,从消息传出的一瞬间开始,连续数日,微信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悼念。声浪之大,情感之真切,我身为任洪渊的学生,也不禁惊讶,为之动容。尤其是,其中有很多都是和任老师并不算熟悉甚至从未谋面的年轻一代诗人。可是,任老师生前,其实并没有得意于文坛和诗坛,他更是一个踽踽独行的灵魂,一个激烈而又寂寞的属于诗歌和文学的灵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为什么一位83岁老诗人的去世,会令那么多诗人和学者有那么强烈的惊讶、不舍和悲恸?
真正伟大的艺术灵魂,越老越强壮
我想,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诗人任洪渊,有一颗仍然年轻的心,依然是一个正在当代诗歌现场的、活跃的创作者和创新者,我们还在等待他的新作继续带给我们惊喜。他并不是那种已经失去了写作活力、失去了创作力、靠着往昔的声名和文学史的位置存在于世,享受着人们脱帽致敬的荣光的那种文学老人。那样的老人,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他和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属于过去的时空。而任洪渊不是。他就在我们写作的现场,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作者,谁能接受一个仍然充满活力的生命戛然而止呢?直到噩耗传来,很多人才意识到,原来任洪渊真的已经80多岁了,虽然他仍有雀跃和激荡的心,但包裹这颗心灵的身体,却已走向衰竭。
进入21世纪以来,任洪渊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7年完成了《1967: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2010年完成了《很少有哪一个少女的身姿,不被乐善桥曲线无情地解构》;2011年完成了《1971:雪,致萨哈罗夫》;2012年完成了《1972:黄昏未名湖》;2014年完成了《1974:明十三陵》;2016年完成了《远眺卡拉瓦乔20岁的脸》——每一首都是杰作,贯穿在任洪渊的70岁到80岁之间,每一首写得都像重金属的打击乐。
“我悲怆地望着我们那一代人,虽然没有一个人转身回望我的悲怆”
“剑锋,还斜横在胸前,乱发的断头,提着,停在落日掷地前沉重的静止”
“我听你雪极无瑕的忧郁,听你,暮色已是曙色的白夜”
……
这样的诗句,如刀枪剑戟般击打而来,令我更加相信,真正伟大的艺术灵魂,越到老年越强壮。更何况,同样在2010年,任洪渊还创作了一首非常重要的史诗《第三个眼神》。这是一首值得被反复分析和研究的诗。在这首既慷慨热烈又深邃沉厚的诗中,任洪渊欲向太阳借取一个跨越时空、洞穿历史、透向未来的人类的眼神。任洪渊逝世之后,新世纪的这些杰作和名句,与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众多名作一起,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如暴雨般流传。从某种程度来说,他正处于创作的盛年啊。奈何天不假年。很多人的痛切哀悼,大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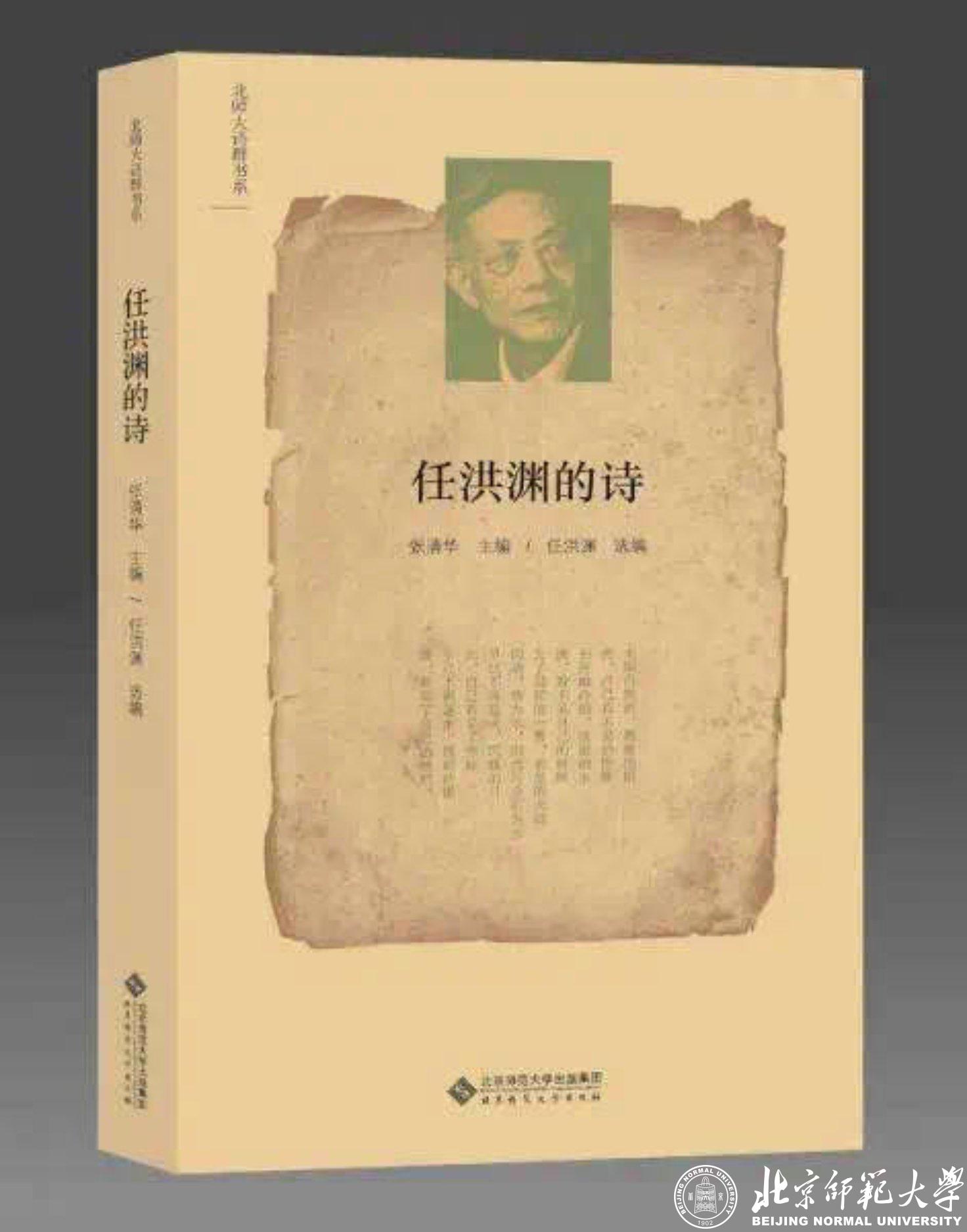
理想化的诗人人格,保全在他身上
另一个原因是,任洪渊身上保全着一种理想化的诗人人格,当代中国的一种罕见的诗歌形象:干净、纯粹、骄傲、天真、激越、浪漫。这种经典意义上的诗人形象,几乎来自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诗人对自身形象的想象以及大众对诗人理想形象的想象。而任洪渊,正是这样一位跨越世纪的存在——他仿佛是从19世纪而来,穿行过20世纪,又在21世纪继续塑造着自己的形象。这是一个惊人的罕见现象:一种想象中的、往往是被刻意塑造和夸大的理想化的诗人形象,完整而天然地保全在一位仍然活跃创作的当代诗人身上。
这几年来,任洪渊参加“新世纪诗典”和“磨铁读诗会”的一系列诗歌活动时,每一次亮相,都构成了某种精神层面和诗人人格层面的展示,年轻的诗人们为此肃然起敬。他们当然分得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刻意的;什么是清澈的,什么是浑浊的。诗歌说到底,是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事。任洪渊的每次出现,自然都会构成这样一种感召力,而且是一种珍稀的感召力。所以任洪渊的去世,才会令很多诗人有一种强烈的失去感——我们的时代失去了一位典范的诗人,失去了一位拥有理想化人格的诗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灵魂。
他教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半壁江山
任洪渊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老师。我在这里所说的老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虽然他长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确实也是一位老师。但此老师非彼老师,任洪渊先生是诗人们的老师。在8月18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代表他的众多诗人弟子致悼词时说,任老师教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半壁江山。这么说当然会有人认为我过于夸大,但我自己知道,没有夸大,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半壁江山。伊沙、侯马、徐江、桑克、宋晓贤、朵渔、南人、沈浩波……都是任洪渊的学生。诗人老师和诗人学生,往往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在任老师去世后,有诗人看到我和伊沙不断用诗文表达哀思,感慨道,伊沙和沈浩波不愧是北师大的学生,对老师这么尊敬。我觉得这位诗人理解错了,这跟我们毕业自哪所学校没有关系,也不是对每一位授课老师,我们都会如此尊敬。怎么可能呢?性格如此桀骜的诗人,不会仅仅遵从世俗的师生之义。这么一群骄傲得无以复加的诗人,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认可任洪渊先生为“老师”,哪里仅仅是给我们上过课那么简单。恰恰相反,任洪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并没有试图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写诗,采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技术,没有这些,诗人也从来都不是教出来的。我们每个人日后的写作之路,都与任洪渊的诗歌美学没有关系,各走各路,各行其是。

任洪渊与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更深刻的灵魂意义上的关系。当我们进入大学,憧憬或立志要成为一名诗人时,有人告诉我们说,北师大中文系有一个诗人,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诗人,看到了我们的老师任洪渊,他几乎全然就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诗人,那么骄傲,那么不肯屈从,那么怀抱热情,那么激越,那么干净纯粹。还有比这更深刻的教育吗?他的每堂课,每次讲座,每回和他私下的交谈,都是一颗诗歌的灵魂在闪耀着光芒。更重要的是,他一生都如此,至死未改变,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世俗如何强大,我们的任老师,没有变化。诗人就当如此啊,至少对于我来说,这是烙印在灵魂深处的教育。
迎着死亡冲刺,写作心灵自传
在生命的最后,他还在给予我们教育。一直到弥留之际,他仍在写作,在写他一直未完成之心灵自传。他已经不可能有力气再握笔写作了,那就用口述的方式;而疫情期间,外人全都不被允许进医院探视,那就在电话里口述。他的助手王少勇先生,和年轻的女诗人里所(是他学生的学生)承担了记录其口授的工作。任洪渊口授出的文字,无需修改,直接就是完整的成熟的文学语言,每一句他都已在心中打磨好了腹稿,精确到每一个标点,经常还会在后来的口授中对此前的口授进行修改——他每一句都记得。这是多强大的心智呵,若非身体已经衰老,仅就灵魂而言,他仍在盛年。如何面对死亡,如同将生命奉献给创作,何等惊人的意志……还能有比他更好的老师吗?
由于我在北京,离他较近,在众多诗人弟子中,最近十几年来,任老师与我联系最为紧密,叮嘱得也最多。有两个叮嘱是他一再重复的。一个是劝我不要太桀骜尖锐,不要太得罪诗坛。我当然知道,他是在担心我,怕我这怼天怼地的性格,会被诗坛孤立。我在心中暗笑,任老师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却希望我能做到。其实,任老师就是担心我重蹈他的覆辙,他就是一个始终被搁置在边缘的诗人啊,这当然是因为他的性格。他太天真,不懂得也学不会世俗层面的利益交换那一套。他又太骄傲,就算明白,也不能容忍自己去做那些世俗之事,谋取世俗之利。他不是不想要现世之名声,他当然也想要,也想让自己的创作能获得更多层面的认可和褒奖,但他这么天真和骄傲的性子,学不会搞不懂也不肯低头去换取。任老师对我的另一个劝告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诗被翻译成更多语言,在国际上发表和出版。有一次,他甚至专门给我打电话叮咛此事。我知道,这也是他自己的遗憾,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有多好,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世界看到。他对我的这两个劝告和叮嘱,其实都是不希望我重复他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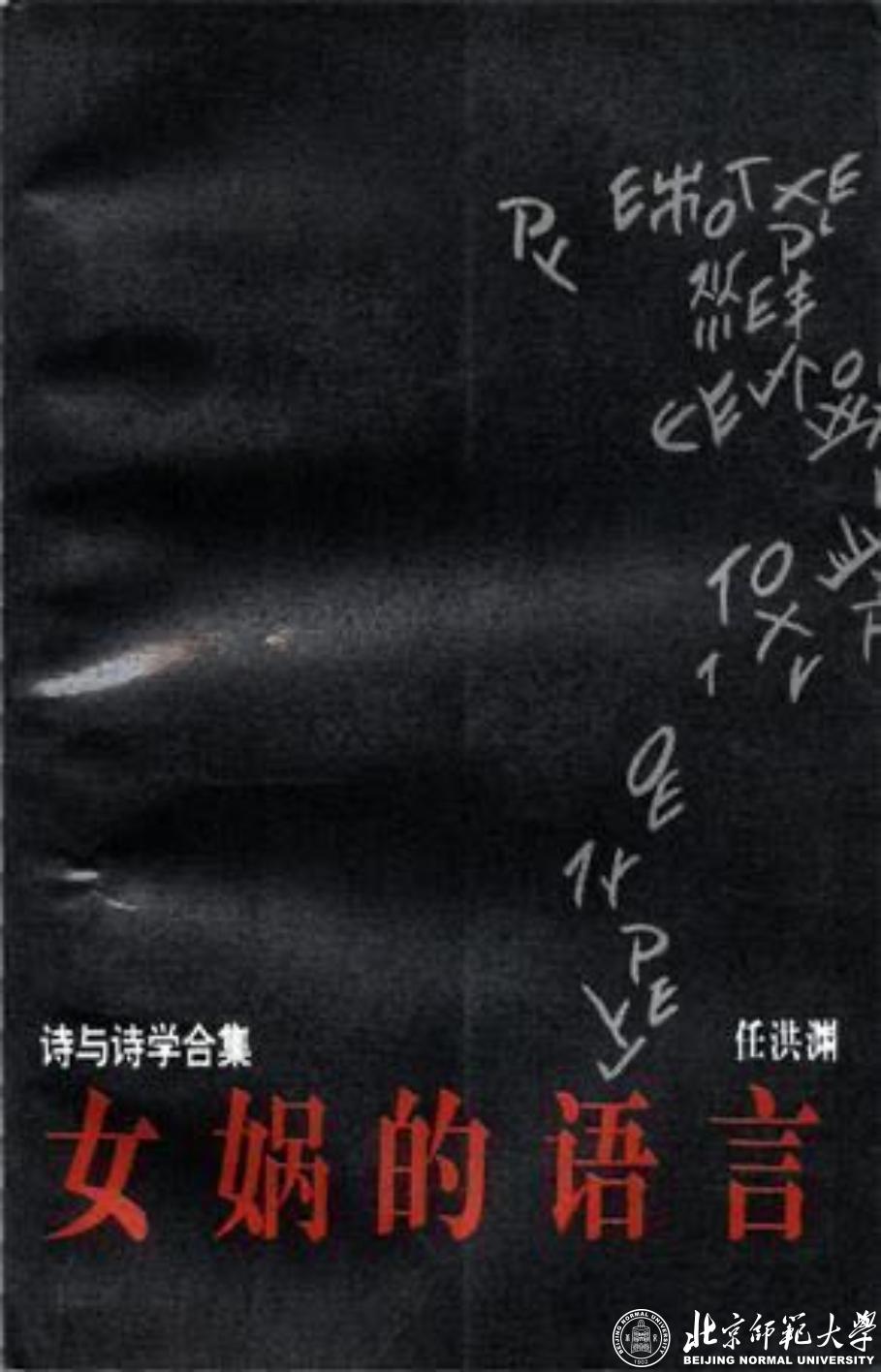
我想对任老师说,在世时您或许寂寞,或许未被广泛重视,未被真正认知。但有什么关系呢?您独特而杰出的诗歌作品,瑰丽的文化哲学著作,一定会在时间的长河里,越磨越亮,熠熠生辉。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有过任洪渊这样的诗人,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最后,用我的一首悼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冲过死亡线
——记诗人任洪渊的最后时刻
身患癌症的老诗人
自知时日无多
放弃痛苦的治疗
要与老天抢时间
完成一部自传
他已无力打字
在病床上打电话
口授给弟子
多么疯狂的欲望?
——他要让自己
留在时间里
他正是这样的诗人
不但有资格
而且有办法
强行让自己
活在时间里
不肯
去死
还有比这更酷的吗?
当他迎着死亡冲刺
2020.8.13
任洪渊(1937.8.14—2020.8.12),诗人,生于四川邛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1届毕业。1983-1998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墨写的黄河》、多文体书写的汉语文化哲学《汉语红移》、诗集《任洪渊的诗》等。